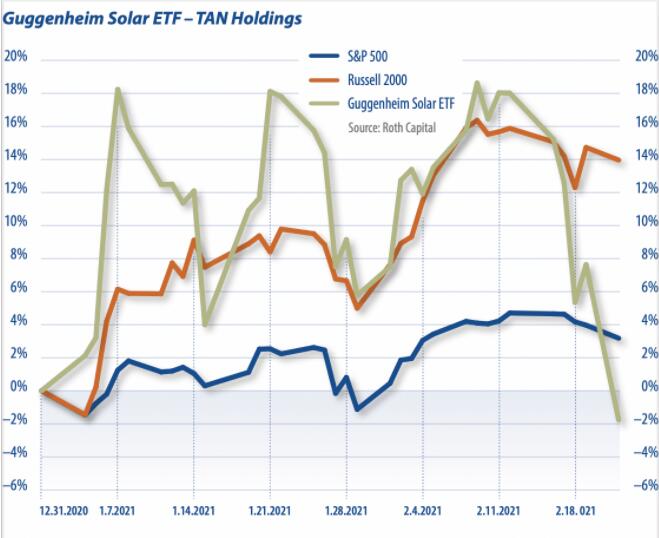“鲟梦者”危起伟:无比期待十年后的长江
本报记者 赵征南 驻鄂记者 钱忠军
随着十年禁渔的推行和《长江保护法》的实施,长江大保护又一次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焦点。
长江如母亲慷慨地给予人们一切,却也因人们的过度索取而伤痕累累。长江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这是多么沉重的话语。
长江究竟还剩多少种鱼?在距上一次长江渔业资源全面调查的40多年后,从2017年起,国家有关部门设立专项资金,部署开展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工作,流域内相关研究所和高校等共20多家单位共同参与,该调查的首席科学家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危起伟。
危起伟是农业农村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鲟鱼专家组成员,其主持完成的“中华鲟物种保护技术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他向记者透露,专项调查已经基本查清了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家底:长江流域历史上分布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鱼类有435种,约占我国淡水鱼类种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此次专项中采集到的鱼类仅有311种,占历史分布鱼类总种数的71%。同时,还有一些好消息,包括多年未见的鱼“突然冒出来”、2020年鄱阳湖刀鲚数量增长等等。
“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长江经济带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危起伟相信,随着长江生态综合保护措施逐步到位,长江水生态环境未来将显著改善, “十年后的长江,我无比期待”。
建成单体最大的鱼类迁地保护人工水体
盯着游来游去的鱼儿,看一整天都愿意
“中华鲟陆—海—陆人工保种繁育基地项目正全力推进,直径66米,水深4米,水体量9000立方米,这个巨型中华鲟仿自然巡游地将成为世界上除商业海洋馆外,单体最大的鱼类迁地保护人工水体!”
“农业农村部召开常务会议,聚焦实施拯救行动计划、加强珍稀濒危物种资源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等重点任务,加快推动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项目落实落地。抓紧建立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网络,做好长江禁捕效果评估和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审议并原则通过《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建设方案(2021-2025年)》,这对于保护中华鲟、长江鲟、长江江豚而言,是重大的利好!”
进入3月,伴随着《长江保护法》的正式实施,长江大保护迎来多个好消息,这让危起伟紧锁的眉头舒展不少。61岁的他依然奔波于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各种重要场合。他在上海参会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会议一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奔回湖北的繁育基地。
“如果说搞农业研究的必须要‘下田’,搞渔业研究的就必须要‘下水’,到水边去,到水里去,一直待在实验室里是不行的,实践出真知。”危起伟说,他的工作40年如一日,快乐的时光总是与长江相伴,让他盯着繁育基地里鱼儿游来游去的画面,欣赏一整天他都愿意。
鱼儿是他的命。
时针拨回到1960年,危起伟出生在江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童年在德安县度过,流经县城的博阳河再奔腾几十里地就是鄱阳湖。
他从小在水边长大,印象最深的儿时记忆几乎都与水有关:到了夏天,大人、孩子都聚在河里游泳,看着清澈见底的河水中成群鱼儿从身边游过;外公是能干的渔民,那时没有电鱼、毒鱼,捕鱼就靠鸬鹚,在渔船的桅杆站上一排,逐个下水抓鱼;外婆则擅长烹饪河鲜,在锅里将餐条煎得两面发黄,一勒很容易将左右两瓣鱼肉和中间的脊椎刺分离,一条鱼两口就吃完,那是最美的味道。
年少的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能走上鱼类保护与研究的舞台。
家境贫寒、2次辍学、放了2年牛,当了一段时间学徒,小学到高中累计上学时间只有6年。危起伟为此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成功考入当时的江西大学,专业为生物学。
“那时也没什么职业规划,就是误打误撞。父亲对我选的专业非常不满意,说‘生物学有什么用?’但我坚持自己的选择,大学期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本校和外校的专业课本都被读了个遍,并着重加强了外语的学习。”他说。
毕业时,他从南昌前往沙市,进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工作,“那时上大学都不问家里要钱,所有的钱都是国家出的。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的态度基本都是‘服从分配’”。
选择水产,并非他的志向,可他却坚持了半辈子。
从自然中学习中华鲟的奥秘
最初对死去的中华鲟无感,慢慢地会流泪
从进长江所的那一刻起,危起伟就与鲟鱼结下了不解之缘。
起初,危起伟对鱼儿还谈不上“感情”。
上世纪80年代,坝子下、码头边,经常能发现大型鲟类的尸体。他第一次接到任务——“于长江宜昌段的江边船厂将一条死去的白鲟拉回”,看着眼前的尸首,心里还没有波澜,只是静静地想着如何将这个庞然大物带回实验室解剖,“中华鲟死了、长江鲟死了、白鲟也死了,就一个感觉,大。至于感情,都是慢慢培养的,原先根本无法体会这种珍贵。”
危起伟最为人称道的贡献,就是在中华鲟保护上的不遗余力。
中华鲟是一种江海洄游性鱼类。它古老到和恐龙同一时期,最早出现在1.5亿年前的中生代,是个体最大、生长最快的种类之一,有“长江鱼王”之称。虽然生长快,但性成熟较晚,中华鲟产卵量较低,卵的死亡率却非常高,因而弥足珍贵。
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流后,国内有关单位聚集在葛洲坝下,开展中华鲟自然繁殖状况调查和人工繁殖工作。1984年,危起伟加入长江所旗下的资源室资源组,正式接触中华鲟,对中华鲟资源和产卵场调查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率先完成了利用标志回捕法对1984—1985年长江干流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估算,以及中华鲟繁殖群体结构特征分析等。
1983年秋天,葛洲坝下中华鲟人工繁殖获得初步进展,1983—1986年每年进行野生中华鲟江边拴养人工繁殖,并进行苗种培育和放流。到了1986年,很多人都认为,中华鲟人工繁育已获得成功。
但危起伟不是很确信。他试着要了一点鱼苗,可怎么也养不活,多年的野外研究经验让他的脑海中对后期培育产生疑问。后来的结果也印证了他的担忧:每年孵出几十万至上百万仔鱼,却因开口及后期培育成活率极低而被迫实施放流。
因经费问题,中华鲟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联合协作被迫中止。此时的危起伟,对中华鲟已经有了深深的感情,看到死去的鱼儿,他会痛心流泪。
他绝不允许自己参与保护的物种消失。1989年,危起伟牵头启动了中华鲟人工繁殖研究,开始租赁宜昌市水产良种场家鱼繁殖和育苗设施,但因孵化和育苗条件很差,中华鲟大规模育苗难关到1991年都未能突破。
怎么办?中华鲟的秘密必须要去水里寻找。“野外调查很枯燥,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愿意做,但大自然的奥秘恰恰蕴藏在生态学里,我们必须学会从自然中学习。”危起伟想进一步开拓自然繁殖生态研究,但困难重重,“我们科技装备极为匮乏,一个实验室有一台显微镜就不错了,流速仪还是机械的,就连水下使用的胶布都没有”。
由于英语较好的缘故,危起伟和前来中国考察的国外专家博伊德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他充分利用博伊德带来的多套超声波跟踪设备、测深仪、照度计、GPS、尼龙绳、采卵网、螺丝、螺帽、卡子、黏胶等专业器材,并争取到了前往国外数十个鲟鱼孵化场和养殖场考察的机会,创新了中华鲟苗种培养技术——比如池底绝不能粗糙、为方便洄游将长方形改成圆形等。
危起伟于1997年解决了中华鲟培育成活率低的技术难题,开始建立中华鲟人工群体,并于2012年突破中华鲟规模化全人工繁殖,这对中华鲟规模化增殖放流、保护和物种进一步延续等具有重要意义。
为中华鲟研究不间断,婉拒免费赴美读博邀请
时隔40多年后长江专项调查启动
从博伊德的身上,危起伟不仅学到了有关鱼类生态和行为学的知识,更学到了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对科学的献身精神。
危起伟至今都记得1993年10月30日那一天,那是踏遍荆棘后的幸福时刻。当年10月,在首次遥测跟踪试验中,危起伟成功标记并放流了2尾性成熟的雄性中华鲟。但作为当时长江中可以找到的最适合放流的船,宜昌市渔政执法船航速较慢,怎么也追不上放流后的中华鲟,不到1小时后,信号就消失了。所有人都表达了遗憾,博伊德也在1周后离开了中国,但危起伟不甘心!
他租用一条长约6米,马力为5—8匹的柴油挂机木渔船,将水听器绑在渔船桅杆上,让渔船关掉发动机,人工用船桨控制方向,随水流向下游漂流。30日,浑厚的声音从耳机中传来,消失的信号声音终于再现,“咚咚,咚咚咚咚咚……那声音真的太美妙了!”中华鲟找到了,危起伟欣喜若狂,持续跟踪,首次监测到了中华鲟繁殖的准确位置,并完成了第一篇中华鲟生态学研究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上。
博伊德获知后,更加看重危起伟。从1994年起,便多次邀请危起伟并愿意全额资助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这在当时是很多大学生的梦想。但美国要求读博士必须在校至少2年,期间不能离开,这样国内的中华鲟研究工作便会间断。”
他婉拒了博伊德的好意。
读博的事情一拖再拖。1999年,危起伟遇到了恩师曹文宣院士,2000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博伊德作为第二导师。为了不耽误中华鲟的研究,两位导师批准他以中华鲟自然繁殖生态研究作为博士研究课题,不必再做其他实验。
“曹老师治学严谨,非常务实,很多事情不仅仅是口头呼吁,他一定会亲自下去做调研,为治理‘长江病’提供科学支撑。”此时的危起伟,除了坚持中华鲟的研究,还把关注点放在了宏观的长江大保护上。从2006年起,危起伟也参与到制订《长江保护法》、推进禁渔等呼吁和调研过程。
在两次长江干流宜宾至上海渔民捕捞调查中,他发现长江的实际捕捞量和真正的传统渔民已经非常少,“人们吃的鱼,绝大多数都是人工养殖;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一辈传统渔民已经逐步‘退休’,‘渔二代’的捕捞技术和捕捞意愿与父辈已不可同日而语;同时,非法捕捞、骗取柴油补贴等行为屡禁不止”。
经过调研,危起伟认为,影响长江生态的因素有很多,水坝阻隔、城市建设、航运采砂、工农业污染等,禁捕或许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一种,分步禁捕在操作上也容易执行。
更多的本底调查在长江全流域铺开,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系统开展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水域生态修复的基础。
上世纪70年代,长江六省一市曾开展过一次水产资源调查,其后,虽然有专题或区域性的调查或监测性工作,但并无全面深入的了解。
几十年来,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变换资源密度估算,长江重点禁捕水域(一江两湖七河)鱼类资源现存数量为12.07亿尾,重量为11.74万吨。历史上渔民在长江一年天然捕捞峰值为1954年,为42.7万吨。换句话说,如果按1954年的捕捞量,如今长江中的鱼3个月就会被捕捞完。
综合历史资料,长江水系共分布有鱼类435种,包括420种土著鱼类(含374种淡水鱼类、8种洄游型鱼类、38种河口定居鱼类)和15种外来鱼类。2017—2019年专项调查实施期间,历史有分布而本次专项中未采集到的鱼类有124种,占历史分布鱼类总种数的29%。
“并不是说未采集到的鱼灭绝了,但意味着总量已不多。若不严加保护,或许难逃厄运。”危起伟表示,本月将就相关科学调查结果进行专家评估,今年将发布长江渔业资源环境本底调查结果以及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的评估报告。
精灵们未来将走向何方呢?
长江的鱼儿们,一定会再回来的
为了挽救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1月1日,长江流域正式开始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11.1万艘渔船、23.1万渔民退捕上岸,开始了“人退鱼进”的历史转折。人们关心的是,十年后,长江会重现昔日生机吗?
“禁捕只是一个‘抢救方式’,未来长江大保护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十年休养生息后,长江渔业中土著鱼类的产量会逐渐恢复,但不可能再回到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而许多濒危物种的恢复可能会更困难。”危起伟说,“长江鲥鱼消失得太快,我们都没能来得及攻克人工繁殖方法;此外,白鱀豚和白鲟也相继宣告功能性灭绝。”
去年年初,他所撰写的论文《白鲟的灭绝给长江生物保护留下了什么教训》,让白鲟以一种“初闻即是永别”的惨烈方式引发社会关注。
白鲟是长江的一种特有鱼类,有着梭形的躯体,其头长超过体长的三分之一,吻部则占头部的近五分之三,突出如剑。成年长江白鲟个体最重可达500公斤,体长能达7米,在长江渔谚中被称为“万斤象”“水中老虎”,可一口吞下七八斤重的草鱼。
危起伟还记得最后一次目击白鲟的场景:2003年1月,四川宜宾江段,一条长3.52米的白鲟误入渔网被误捕。渔业部门现场查看,白鲟为雌性,身上有长约8厘米的伤口,腹内有鱼卵,急需救治。他和团队成员直奔四川,对白鲟进行消毒和伤口缝合,待伤势好转将其放流,并在它身上安装了超声波追踪设备,但后来由于追踪船触礁损坏,正值春节无配件修复,最终失去了信号。此后,国内再也没有长江白鲟的目击报告,也无一活体踪迹。
“绝不能让中华鲟等珍稀物种重蹈白鲟的覆辙。我们要保护好中华鲟人工群体,实施陆海陆接力保种群体健康发展,突破一批理论和技术创新,如实现人工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繁殖。另外,近期要实现长江鲟自然繁殖,重建长江鲟自然种群。”危起伟表示,在长江专项调查中,中华鲟、长江鲟、胭脂鱼、川陕哲罗鲑都没有自然繁殖活动发生,“对于中华鲟这类古老物种而言,它比较‘顽固’,不可能在短时间做出适应性改变,产卵场更改的可能性比较小,更大的可能是没有自然繁殖。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自然种群将走向绝迹”。
长江生态是渐变过程,要恢复非一日之功,十年对于长江大保护只是序章。
“与我刚进入这个领域时相比,我国在科技装备、技术理念上已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宏观规划把控层面,甚至可以说一枝独秀,这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危起伟真切地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6年1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后,长江水生生物的保护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长江专项调查为例,2016年相关部门是主动作为,2017年立项启动。”
在“一盘棋”的影响下,整个社会对于长江保护的重视程度明显加强。“过去,人们讲究吃野味,我为制止别人捕捞江鲜被别人打过,周围人说我‘又不是你家的,凭什么不能捕’‘多管闲事’。现在这种情况已不可能出现。而且受学校生态教育的影响,下一代人基本告别了‘吃野味’,他们会主动加入到生态保护的队伍中。这是最令人欣喜的。”危起伟说。
去年年底,长江水产研究所科研团队开展野外科考时,在长江公安江段采集到7尾“消失”多年的鳤鱼;同时,去年鄱阳湖的刀鱼种群密度变大,多处疑似产卵场被发现……一系列的信号让危起伟相信,随着各项保护措施的落地,长江生态系统会逐步恢复健康,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将恢复到良好水平,长江大保护的目标终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