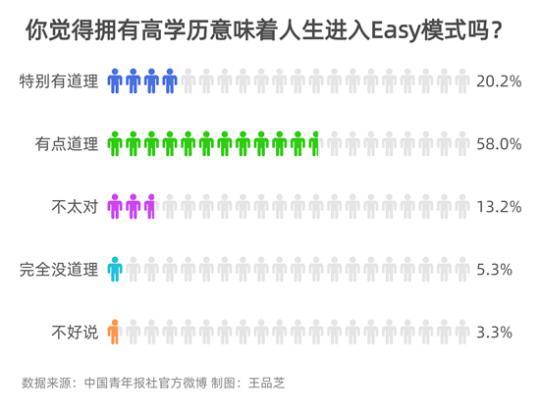人们是被不同的记忆拽回到2020年的。
3年来第一次回家的留学生,上飞机前得知妈妈发烧住院了。之后的好几个星期,她都得不到妈妈的任何消息,只能在手机上看滚动的新增确诊病例数,每天刷好几遍。她知道,那些确诊数字里有一个是妈妈。
没抢到回老家车票而留在武汉的外卖小哥,瞒着女友每天在外接单。疫情期间,他骑着车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送过餐、菜、药,最喜欢的还是帮人喂猫,他回不了家,但替别人回了家。
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里,护士长已经至少20天没休息了。病人很多,走廊和大厅里都是病床。她对着镜子剪了头发,然后给科室里几个留下来的年轻护士也剪了短发。他们守着楼,和病人一起等待增援。
这些武汉疫情中的故事,被写进一部声音剧里。剧里一共7个角色,此外还有被感染的母亲、在武汉一线的记者、值守社区的社工、外来援鄂的医生。
这部剧没有专业演员出演,每一个角色的故事写在一张纸上,交给报名参加的普通人在台上读出来。从去年6月至今,这部剧演出了68场,一路从上海、长沙、深圳、天津,再到北京,共有476位观众作为演员参演。
剧的名字叫做《回家》。上过前线的医生,留着胡子略微发福的中年大叔,穿格子衬衫背书包的学生,拎着名牌手提包的年轻白领一一登台。最小的只有10多岁,年长的已70多岁。没有事先的排练,可无论是台上的人还是台下的人,多数时候,只要两三句台词开场,就进入情景,回到疫情的记忆中。
1
故事在7把椅子围起来的一片安静小空间里展开。
台上的演员大部分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有人带着天南海北的口音,有人打了嗑巴,也有人突然哽咽到读不下去,平复了几分钟才终于继续。
舞台的灯光尽可能调暗,就连话筒也不用。45分钟的演出时间里,舞台全部交给普通人。观众报名参加演出,然后,他们随机抽签获取那个载有角色命运的信封,直到演出前才能打开。
艺名“水晶”的爱丁堡前沿剧展策展人是《回家》的戏剧构作、导演,她想出了这种设计。她说,这就像疫情面前每个人的状态,“在疫情最肆虐的时刻,每个人都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定居武汉的谢亚鹏在深圳参与了演出,读剧时,他想到了自己。疫情暴发前他已订好回老家贵州某县的高铁票,回老家后,接触了不少亲朋好友。后来,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他一下变成老家最特殊的个体,“就像一颗原子弹在原地炸开”。
武汉的医生朋友半夜给他打来电话,医院的病床躺了很多人,没位置的就躺在通道里。好多人躲在办公室里偷偷地流泪,谢亚鹏和朋友两个人也对着电话哭了半小时。
谢亚鹏听说,一位中年女人和她的哥哥、父亲都被感染了。她没有中招的儿子辗转在各个医院,一一了解家人的病情。她的哥哥在外地发展,春节为了陪父亲才回到武汉。后来,哥哥和父亲不治离世。她康复后悔恨地说,真不该让哥哥回来,说着失声痛哭。
谢亚鹏的朋友里,有听闻疫情立刻赶赴一线的整形科年轻医生,也有人在基层工作,那些日子几乎无休。有时,他们会在打给谢亚鹏的电话里说,“自己又赚了一天活头”。
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记者章嘉骅在长沙参与了表演。他读的是外卖小哥的剧本。剧本里的外卖小哥穿梭在武汉空荡荡的街道上送餐、买菜、送药。送药的单子让外卖小哥很紧张,跑得飞快也觉得来不及。有时候一个药店没有,要去另外一个,经常跑三四个药店才能买到。
这让他想到武汉刚封城的时候, 他没防护用品,仅靠朋友捎回来的20个口罩生活。他听说,有人居家期间瘦了30斤,还有人因为害怕整晚失眠,单位打了一天电话都没接。为了出去采访,单位给员工发了通行证。那天,食堂的超市被同事们搬空了。
作为武汉人,去年春节,他一个月没见过父亲。两人在不同小区,隔着30多公里,除夕那天,他坐下没多久,父亲自觉身体不舒服,让他“赶紧走”。
拿到单位的通行证出门工作那天,他顺便去看父亲。小区的大门被封,两人隔着高高的台阶远远相望。80多岁的老人独居,封城后没防护物资,章嘉骅扔给他一包口罩。
第一次外出,章嘉骅的车因为太久没开,电瓶没电,他只好骑上自行车出门,花了5小时骑行60多公里,碰到的人不超过10个。
他经过汉阳公园,原先那里总有人跳广场舞、下棋或打牌,还有票友唱楚剧。公园离户部巷小吃街和老商业街司门口不远,平日里外地游客很多。可在那些日子,一向热闹的街边冷冷清清,路旁码着成堆的共享单车。在安静的江滩口,有司机实在耐不住静默,按了几声喇叭。
他后来得知,自己有同事刚刚退休患了新冠肺炎,武汉解封后,对方去世的消息传来。一位年轻的女孩在社交网站上更新日记,她父母都因疫情离世,女孩的父亲也是他的同行。他认识的一位剧作家居住地附近有个老年文艺团,后来,12个人里只剩下了6个。
2
7页纸里,写下的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
比如,被安排到社区支援的基层工作者,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还常常被电话叫醒。除夕从家里饭桌上离开的援鄂医生,忙到忘了自己生日,却收到病人家属送来的蛋糕以及女儿拍手唱生日歌的视频。
这些片段不少源于生活。2020年年初,《回家》剧目的主创团队都被关在家里,他们决定写一个与疫情有关的故事。
水晶认识的一名记者身在前线,总发微博记录心情,她也跟着看那些只言片语,在脑海里拼凑对方的生活。她看电视,一位上海的年轻医生在酒店里疲惫地接受访问,记者问“疫情结束后想干吗”,他说就想平常地上一天班,平常地回到家里,平常地坐下跟女儿吃一顿饭。
她被那些小人物击中,决定写写生活中那些平常角色。
《回家》的编剧刘芯伶看过不少关于武汉的纪录片,也采访了自己在武汉的朋友黄丽峰。黄丽峰在湖北省文联工作,她春节去湖北某市农村的婆家过年,看着新闻里确诊人数上涨会突然哭出声来,她不敢晚上看新闻,否则会睡不着。
后来,她接到消息要下沉到村子里值守。有时值守点只有她一人,她搬来家里的椅子横在土路中央坐着,北风呼呼地吹。没有防护服,她穿一次性的雨衣把全身包起来。
她的工作从正月十五开始,持续了1个多月。3月底回到武汉,居家隔离14天后,黄丽峰从单位得知社区还需要人值守,她又加入队伍,赶往硚口某社区。
简易的棚子搭在小区门口,挂上红蓝条纹的塑料布,再找来砖块压住塑料布脚,勉强可以挡风。她和同事从社区办公室搬了两张桌子、几把椅子拖到棚子里,几个人上岗了。
她和小区的保安共同为出行的居民量体温、做登记,有时也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给老人送东西,对康复回家的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做回访。她教老人用智能手机,设置健康码,几天里来来回回讲上好几次——不少老人前一天学会了,第二天又忘了。
刘芯伶问黄丽峰怕不怕,她回答,没时间想怕不怕,只有夜里躺在床上才有空回想一天的经历,“那是后怕”。
在微博上,刘芯伶关注了不少“超话”,也帮忙转发过求助帖。她关注过一个人,曾为他父亲发过一条条求助消息。后来,他刚接到有空闲床位的电话,父亲就离世了。
有一天夜里,刘芯伶刷着微博,突然看见了那人发了一条动态,“爸爸,我想你了”。在发求助帖之前,那人发的微博寥寥可数,如今接连写下的零碎文字都与父亲有关。那是几个月后,他还没走出失去至亲的痛苦,但新发的动态已经没什么人评论了。
“疫情给个人的痛苦实在太重,也太长远了。”刘芯伶感慨。
他们没刻意地在剧本里设置泪点,不过,观众会在不同的地方自己开始崩盘。有时是开演两三分钟,就传来断断续续呜咽声;有时一场下来,中间总要停上好几次。在水晶的印象里,没一场演出冷场,也从未有观众提前退场。经常是活动链接发出不久,观众的预约就已满额。
一开始,演出结束,观众总是恋恋不舍地留在原地。有人举起手里的那页纸仔细端详,也有人三三两两地扎堆儿分享。主创们干脆设置了半小时的分享环节,让参演的、围观的观众都聊聊自己的体会。
一位前来看戏的中年男子表示,自己不在武汉,看着一线的消息,在家里也没少掉泪。一位年轻姑娘在一次演出中拿到护士长的角色,没开始演时已仰着头流泪。她说自己就是护士,曾报名加入第一批援鄂的队伍,遗憾没被批准。
3
有时候,戏里的角色和戏外的人生是重合的。
几名本就是护士的观众拿到了护士长的角色,也有记者碰巧读了记者的那段独白,参与演出的,还有在武汉做过疫情救援的人员、外出留学回国不久的年轻男女。
拿到患者剧本的滕岚,平日在北京一家医院做心理医生。疫情期间,她所在的医院并非定点医院,但也承担抗疫任务——这些医护人员要外出为社区居民做核酸检测,去隔离点当助手,在组建的发热门诊、用于核酸检测的PCR实验室中值守,包括最近的疫苗接种,一年里几乎都围着疫情转。
穿防护服,戴护目镜,握额温枪,她再熟悉不过。她习惯了晚上10点接到任务,第二天早晨8点直接到位。她加入一个又一个群里,有的任务她出过好几次。
2020年6月,她所在的医院第一次集体外出,为社区居民做检测。三伏天里,她和同事套着防护服一连工作两个多小时,还赶上了一场狂风暴雨。
在露天的广场上,雨水倾泻而下,他们把样本箱护在遮阳棚底下。水越积越多,压得棚顶快塌了,前来的居民和他们一起给棚顶排水,还帮着搬东西,有人早已完成检测,怎么都劝不走。
李欣曾朗读护士长的剧本。作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首席主播,她负责的工作之一是播报新闻。2020年初的一天,她正报着数字,突然看到确诊人数大幅上涨,一下哽咽。
一位上海杨浦区援鄂医疗队的护士长和她讲,队里的护士去救一个年轻人,进手术室前,对方的手机响了,她帮他放到保鲜袋里装好。那个人死后,护士还一直帮他按着胸部,坚持一定要救他回来。保鲜袋里的手机屏幕一次次亮起来,没人知道那头有谁的牵挂。后来,这个故事也被写进了剧本里。
疫情之下,也有温暖的故事。章嘉骅朋友的亲戚封城时被困在广西,住酒店期间遇上一位湖南人,那人给他点了一桌菜,说湖北人今年不容易,尽量吃好点儿。
谢亚鹏曾一度自责。离开武汉前,没疫情的消息,他主持过几场上百人的活动,感染的风险不小。他试探地问老家和他接触的堂哥怪不怪自己,对方给出轻描淡写的答案,一家人不就该有难同当吗。
他的一位朋友患了新冠肺炎,所幸是轻症。在方舱医院里,这位患者遇见了来自内蒙古的援鄂医生,对方从病情登记卡上看到了两人同年,安慰患者别担心,“以后我们每年联系,都要好好地活着”。
4
不少人坦言,如今关于疫情的新闻仍在滚动更新,但自己不会每条都点开了。
对于疫情,所有人都在慢慢习惯,也因此慢慢改变。那位曾经发帖求助的博主,在父亲刚离开的那段日子,看见和父亲年纪相仿的身影,他总会禁不住鼻酸。他评价父亲“一辈子老实本分”,父亲这两年曾在建筑工地做工补贴家用,有一回被施工坠落的零件打破了脑袋,也只默默回家歇了几天,怕麻烦没找对方赔偿。
他最难过的是父亲没能跑赢时间,很快,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投入使用,床位不再难求。如今,父亲离开已经11个月了,他尽力找回曾经的生活,给自己改了昵称“坚强如斯”。
黄丽峰撤出社区的那天正是周五,接下来的那个周一,她就要回湖北省文联上班了。那天回家彻底地洗了澡,洗完所有的衣服,她和家人报了句“平安”。
她躺在沙发上看电影,慢悠悠地享受那个晚上,迟迟不舍得睡。她说,那是疫情暴发后她最轻松的时刻。
疫情后的第一次朋友聚会,谢亚鹏在举杯时说了两句话,“新年快乐”,还有“庆祝我们都还活着”。一桌人淡淡地讲起疫情初期的故事,有人眼眶含泪。
6月里连着3天,他做志愿者的武汉血液中心办活动,感谢疫情期间的无偿献血者,人们登船游长江。船上只有一个乐队演出,和观众隔着长长的距离。萨克斯吹起来,江边灯光闪烁,他才觉得这座城市真的活过来了。
他在这里读大学,最开始和多数外地人一样,嫌武汉夏天热,冬天冷,当地人说话太吵,交通过于狂野。后来,他发觉这座城市接地气,人直率,物价亲民,挺适合年轻人打拼。
他选择留下,在3年前买了房,和这座城市一起发展得越来越快——他看着积玉桥告别上了年头的老旧房屋,过江隧道、地铁在这里交会,路宽了,楼高了,车多了。光谷广场不再泥泞,修起国内最大单体钢结构公共艺术品“星河”转盘。
他在5月初回到武汉,出门时习惯揣上几个口罩、带一小瓶用于消毒的酒精。在他身边,有人坦然地谈论生死,也有人买起了各式各样的保险。谢亚鹏决定今年停工,他辞了职,把旅行列上计划,启程去了大理、丽江、广州和深圳。
章嘉骅手机里那个按居住单元建的群,慢慢不再活跃,但每隔一段时间,社区工作人员还是会发来最新的防疫政策。他和朋友们出门,发现小区里开始“鸟进人退”。他常去家附近的金银湖公园,春天已至,波斯菊铺满地面,零星的行人坐在自带的折叠椅上。
刚开心理热线那阵儿,滕岚接到的咨询电话总是充满恐慌。后来,话题围绕着长期居家带来的种种问题,有人濒临破产,也有徘徊不定的年轻人拨通这个号码说,自己一年多没回家了,每次打算出发都碰到疫情波动,老人生病很久,他纠结自己是否还要在北京坚守。
水晶承认,起码短时间内,疫情仍是困扰人们的现实问题,没人知道它会在哪一天突然消失。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部剧会继续演下去。
剧本不对外公开,演出结束后,参与读剧的观众可以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一页。他们还会收到一个小小的信封,那是一张来自武汉的明信片,盖着4月8日的邮戳——那一天,武汉正式解封,这是章嘉骅帮忙提供的。主创们还决定,2021年的这一天,会带着这部剧走进武汉。
章嘉骅在长沙参演的那一次,是解封后他第一次离开武汉。他读到快递员的那句话,“这么大的城市怎么一下子就空了,人呢?”想到自己在空荡荡的城市中骑车的时刻忍不住落泪。分享环节,他一张口又失声痛哭。一位长沙的观众随即站起来大声说,我代表长沙人给你一个拥抱。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滕岚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2021年01月20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