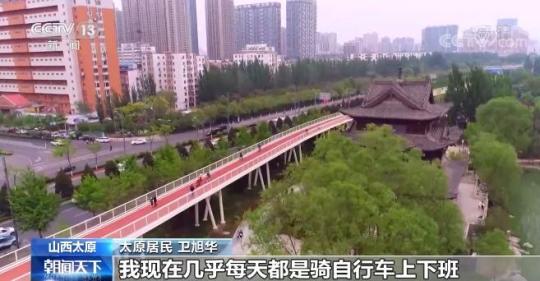“漠河舞厅”往事
“一蹲、二起、三摆架……”
11月6日晚上,中国最北端的小城漠河,55岁的李金宝展示了一段舞技,他搂着舞伴,反身、倾斜、摆荡……旋转在偌大空旷的舞厅中。《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一支慢三舞曲,舞灯时明时暗,摇曳生姿。
10月下旬,一首《漠河舞厅》歌曲爆红,将这家东北边陲小城的舞厅推到了聚光灯下。创作者柳爽介绍,歌曲以舞厅里一位独舞老人“张德全”(化名)和其在大火中失去的亡妻的故事为创作背景。歌曲里忠贞的爱情故事,唤起了人们对发生在1987年的大兴安岭“五·六”特大森林火灾的沉痛记忆。
火灾之后,漠河重建,当地出现了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私营大众舞厅,成为除电影院之外最受当地人喜爱的休闲娱乐场所,也见证了漠河人漫长的自我疗愈与生活复苏。作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众流行产物的舞厅,在漠河被赋予了另一层特殊的意义。
但此后三十多年间,舞厅从顶峰走向衰落,并一度断档,直到2018年,李金宝的舞厅开张。
当年跳舞的人老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轻的“张德全”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座边陲小城,交付半生青春。如今暮年已至,一部分人搬离漠河,还有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来。
由于疫情等压力,舞厅经营惨淡,李金宝一度想把舞厅关了。随着《漠河舞厅》的走红,他改变了想法,“把舞厅开下去,让跳舞的老人们能一直跳下去。”
寻找“张德全”
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半地下室,坐落在漠河的商业区。
入冬之后,漠河的白昼越来越短。下午4点左右,小城暮色四合,地下室门匾上“舞厅”两字的霓虹灯亮了起来。门匾左边竖着排版的“漠河”两个字,还没来得及装上灯带。这是李金宝几天前才替换的名字,在此之前,他的舞厅叫做“梦知艾”。
从台阶下去钻进室内,是一间约400平方米的长方形空间,室内光线暗淡,粉红色灯光撒落下来。舞厅左边靠墙放着一排整齐的座椅,是普座区,平时收费每人5元;舞厅右边几张桌子和椅子组成“卡座”区,桌上铺着绿色的台球桌布,盛放着一盘糖果,收费每人10元。
黑龙江疫情持续收紧,李金宝的舞厅有一阵没有营业了,整个大厅空落落的。
下午五点多,漠河文旅局局长冯广庆来到了舞厅。自从《漠河舞厅》火了之后,他经常来舞厅找李金宝。
他刚来不到几分钟,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裹得严严实实的年轻人探头钻进了舞厅。他操着一口广东腔普通话问道,“这里是不是漠河舞厅啊?”他是柳爽的粉丝,1996年生的小伙子,从深圳飞到哈尔滨,又转乘绿皮火车花了十几个小时才来到漠河,只是为了“见一见真正的漠河舞厅”。
冯广庆有些激动地揽住他,“你是第一个来打卡的粉丝,我们必须合个影。”
冯广庆今年53岁,平时喜欢玩短视频。出于文旅行业的工作习惯,他经常会搜索全网的漠河元素。《漠河舞厅》这首歌他去年就听过,但是没怎么留意。
今年3月,文旅局的视频号曾发过《漠河舞厅》,但没激起什么水花。直到10月中旬,这名年轻人把歌曲背后的这段爱情故事提炼出来,以旁白配歌曲的形式发在短视频上,突然就“火得一塌糊涂”。
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李金宝,显然消息滞后了很多。10月中下旬的一天,漠河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拍舞厅,跟他说:“你这舞厅火了你知道吗?”李金宝一头雾水,“我不知道哇。”记者翻出手机里的短视频,“看这是不是你的舞厅?”
这是李金宝第一次听《漠河舞厅》这首歌,并且知道了舞厅爆红的原因:一位叫张德全的老人在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事故中失去妻子康氏,此后他三十多年未娶,为了纪念爱跳舞的妻子,老人经常来舞厅独舞,老人跳舞的舞厅正是李金宝的舞厅。
看着动图里跳舞的老人,李金宝脑子里浮现出一个人。他告诉新京报记者,2019年的确经常有个老人来舞厅跳舞,别人都是成双成对跳交谊舞,只有他一个人跳独舞。“他还挑曲儿呢。他喜欢节奏感强的,抒情的那种他还不跳。”
但李金宝没有跟“张德全”说过话,并不清楚他的故事。舞厅只开半年,从10月1日开到来年5月1日。去年开始,由于疫情,舞厅开了关关了开,李金宝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张德全”了。
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副馆长马景春也注意到了“张德全”,纷至沓来的媒体电话打到了纪念馆,马景春翻阅了漠河县城范围内的遇难者名单,并没有找到一位康姓遇难者。
《漠河舞厅》制作人柳爽告诉新京报记者,“张德全”系化名,故事加入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想象和细节填充。
虽然“张德全”的故事暂时无法考证,但马景春觉得,“张德全”就是老漠河人的缩影,1987年那场大火发生时,男人们都去了山上救火,遇难者大部分都是留守在县城的妇女儿童和老人。马景春记得,2008年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新馆扩建时,一位开出租车的男人气势汹汹地冲进纪念馆说,“我要看看这馆里有没有我家人的照片,如果有,我都要撕下来带走!”
那时候马景春还是一个讲解员,她带着男人看完了布展照片。发现没有自己的家人,男人悲伤地瘫坐下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这场大火中丧生。
“我太理解他的那种痛了。”马景春说,大火给她留下了长达数十年的心理创伤,她每个晚上都会反复梦到着火和躲火,“那是一辈子都无法忘的记忆。”
惨痛的回忆
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官方资料中记载了这场大火的缘由:1987年5月6日上午到5月7日上午,因清林作业员吸烟将没彻底熄灭的烟头扔在草地上、违规使用割灌机等行为,一共导致五处地方发生火灾,这五起山火经防火部门积极组织力量进行扑救,5月7日中午火场明火被扑灭,火情得到控制。
然而这天中午,漠河境内天气突变,刮起了8级以上的西北风,使河湾、古莲两处火场内死灰复燃。在古莲火场,龙卷风将火舌从地面卷上树梢,火头高达几十米、上百米,火势形成人力不可遏制之势,把扑火队伍逼回县城。
那一年,21岁的李金宝才从吉林老家来到漠河两个月,他不喜欢种地,于是来漠河当瓦工。那一年,马景春还是一名初一的学生。下午她和两个小伙伴在家附近打羽毛球,风太大,马景春不得不把球拍放在绊子垛上,和小伙伴们告别回家。
根据他们的回忆,当时县城的人们隐约感受到了不安。天空笼罩在烟雾中,灰蒙蒙一片,看不到火情,但呛得人直咳嗽。回到家里的马景春焦虑地问母亲,“怎么感觉火要着过来啊?”母亲说:“不能够吧。”在漠河,年年都会发生林场着火,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但从没有蔓延到县城过。
很快,人们察觉到不对劲。傍晚6点左右,马景春和家人冲出了家门。烟雾遮天蔽日,大街上全是拥挤的逃难人流。马景春原本和弟弟牵着手,但被人群冲散了。风卷起漫天的小石子,砸在脸上生疼,马景春顾不上那么多,她扒上了一辆开往部队大院的车。军人俱乐部东面有一块很大的空地,马景春到的时候,已经有两千多人在那里避险了。
当时李金宝原本在家带表弟表妹,大火逼近后,他们随着人流逃向了一百米外的大林河桥下。河边没有易燃物,被认为是最安全的避险地,李金宝跳进齐膝深的水里,躲过了一劫。
5月7日晚8时,从正北、西南、西北三个方向扑来的火头同时会聚在漠河县西林吉镇,镇内大树被风连根拔起,直径1厘米粗的铜质高压线被大风扯断,板皮、棍棒和屋顶上的铁皮瓦一齐被卷上半空,民房腾起数十米高的火焰,浓烟遮天蔽日,火光照得满城通红,整个县城一片火海。
据官方资料显示,“五·六”特大森林火灾火场总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包括境外部分),烧毁林地101万公顷,境内被烧毁的各种房舍达63.65万平方米,受灾群众5万多人,一万多户居民无家可归,211人在大火中丧生,266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烧伤,有的造成终生残疾……
这场持续了28天的大火将漠河县城夷为平地,焦黑的土地上,只剩下突兀伫立的烟囱。
“漠河舞厅”的前世
漠河是中国最北部的一座边陲小城,地处大兴安岭地区,拥有丰富的林木资源。上世纪80年代,大兴安岭地区经济富饶,每到春秋时节,大量外地人涌入大兴安岭,被林场雇用为临时工、季节工。
据多位漠河居民回忆,火灾之前,不少家庭已经拥有了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林场工人是“香饽饽”的工作,每月能挣六七十块。县城里有两家电影院,逢年过节很是热闹。
火灾之后,除了居住的房子,漠河人的生活也一并被烧毁了。
《漠河县志》记载了漠河重建的过程。灾后一年多的时间里,35000多人的建筑大军,奋战250个日日夜夜,建成房屋95万平方米,1万多户灾民全部搬进了永久性新居。被大火烧毁的各种生产设施:包括大型贮木场、铁路专用线、公路桥梁、输变电线路和通讯线路等全部恢复。
1988年10月20日,黑龙江省灾区复建指挥部召开总结表彰大会,宣布“大兴安岭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作取得全面胜利。”
人们心灵和精神创伤的恢复,却更为隐秘和漫长。很长的时间里,有人听不得警报声,有人戒了烟,还有人看到绊子垛,下意识想远离。
在这样的背景下,漠河第一家私人承包的舞厅——“百乐舞厅”在1989年诞生了。
59岁的顾兆发是李金宝的哥们儿,也是漠河最懂舞厅的人,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几家舞厅都当过键盘手,后来又经营了一家舞厅长达10年。
顾兆发记得,最初的“百乐舞厅”开在漠河总工会的二楼,舞厅里设备简陋,放的是卡式录音机,只有一盏舞台灯。简易的舞厅出乎意料地受到当地人的热捧,普座票3元钱,卡座票5元钱,而当年一张最贵的电影票只要2毛钱,一盒火柴2分钱。
市场竞争很快在漠河打响。一年之后,“百乐舞厅”附近,更豪华气派的舞厅“大世界”横空出世。老板请了弹键盘的和吹萨克斯的人,灯光和装修更豪华。“百乐”不甘示弱,也抛弃了原来的卡式录音机,引入现场乐队。再后来,文化局开了一家国营性质的舞厅,也加入了抢客大战。
白天,顾兆发在单位上班,晚上,他一头扎进“歌舞升平”的舞厅。那是正宗的“漠河舞厅”,暧昧旖旎的灯光流泻穿梭在舞厅各个角落,键盘手熟悉时下所有的流行歌曲,同时掌控着灯光的明暗和节奏;歌手得是流行通俗的声线,《走四方》《祝你平安》《当兵的人》《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歌张口能来;舞池中,快四、慢四、快三、中三、慢三……舞步旋转进退;中场休息时,年轻人喊“来一曲迪斯科!”顾兆发拧开录音机,放一支蹦迪曲,调一个动感的灯光,然后往椅背上一躺,喝口水,抽一根烟。
上世纪90年代初,李金宝倒腾起了服装买卖。冬天天黑得早,下午四点多就收摊了,其他店主带着他走进了五光十色的舞厅。李金宝坐在卡座上眼睁睁地看,被人撺掇着走进舞池。渐渐地,他从一开始经常踩到女伴的脚,到后来几乎通晓所有舞步,成了舞厅常客。
16岁那年,马景春考上了漠河本地的幼师学校,全班42个同学都是女生。她形容,每到寒暑假,她和同学们就像是“长在舞厅里一样”,一大群青春漂亮的女孩子走进舞厅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据《经济观察报》2008年的报道,上世纪90年代末,大兴安岭陷入了资源危机和企业危困的“双危”境地,林区大批职工下岗,“买断”后的林场职工离开了漠河。人员流失,舞厅不再处于顶峰状态,最后一家舞厅“大世界”在2000年开春后也“黄了”。
顾兆发跟妻子商量,“要不咱们开一个,我瞅着舞厅还能挣点钱”。2000年8月,顾兆发把“大世界”盘下来,开了一家“满庭芳”舞厅,他掌管舞台,妻子负责吧台。
作为漠河唯一一家舞厅,“满庭芳”经营了十年,享受了最后的辉煌。2010年,舞厅所在的老干部局拆迁,舞厅最终关门。
“开业大吉”
此后近十年,漠河再没有一家大众舞厅。舞友们分成两拨,一部分人投向广场舞的怀抱,还有一部分坚守交谊舞的阵地。社区开了活动室,两派舞友错峰租借,每人收费6元钱,明晃晃的白炽灯,一个能放音乐的录音机,就能尽兴舞上一曲。
李金宝后来承包了一个施工队,休息时间会去活动室跳舞,但总觉得“差点味儿”。有一年冬天,舞友们集资租了一个活动场所跳舞,李金宝认为这是个商机,他想搞一个舞厅副业,一来满足自己的“舞瘾”,二来至少有这一帮舞友是稳定客源,“能赚点钱。”
2018年临近年末,漠河商贸街有一家地下旱冰场关停转租,长方形空间,水泥地,年租金两万元。李金宝看中了这块场地,立刻租了下来。2018年12月28日,他在朋友圈吆喝舞厅正式开张,店门口大张旗鼓地架起了“开业大吉”的气拱门。
李金宝找来顾兆发在舞厅弹琴,还聘请了一个歌手,扣除支付乐手歌手的费用,几乎不剩下什么钱。为了削减开支,他把现场乐队替换成了音响。2019年还能勉强赚一点儿,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舞厅经营惨淡,入不敷出。李金宝一度想把舞厅关了。“要是没有这次《漠河舞厅》的歌儿火了,我最多还能坚持一年。”
李金宝事后复盘,从盈利角度看,经营这家舞厅是一项失败的投资。他建了一个叫做“交谊舞之家”的舞友群,一共46人,年龄在45岁至70岁,收大家月票50元。舞友们自带水瓶、保温杯,也难产生酒水饮料等消费。
漠河冬天最冷能达到零下50℃,年纪大的舞友出行不便,李金宝开着他的7座私家车接送。他体谅他们,“月票才50块,来回打车都要20块了,老年人节约,舍不得。”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李金宝开车出了一起事故,赔了两万多元。但他没打算涨价,“都是一个地方的,处出感情了。今年我儿子结婚,他们来捧场,甭管随的礼厚礼薄,都是心意,我不能辜负他们。”
“把舞厅继续开下去”
11月,东北、内蒙古多地出现暴雪,中国最北小城的气温却罕见地比往年同期暖和,直到11月5日才下了一场“能站得住的雪”。当地人说,今年漠河赶上暖冬了。
而对于当地文旅来说,漠河今年正在遭遇一场冷冬。冯广庆说,2019年漠河的旅游人次是234万,疫情后锐减了三分之二。今年3月起,漠河机场因改扩建施工停航一年,旅游业更是受到直接冲击。
今年上半年,漠河文旅局到南方几座城市做了七场线下旅游推介会,下半年因为疫情,线下推介会取消了。而《漠河舞厅》的爆红,让网民关注到这座东北边陲小城。冯广庆知道,这是上天给漠河的机遇,比多少场线下推介会更有用。
话题发酵到1亿浏览量时,冯广庆开始密切关注着舆情,向上级部门汇报。李金宝的舞厅他有印象,疫情检查时他去过几次,冯广庆立刻上网搜到舞厅的联系方式,向李金宝询问了“张德全”的细节。
李金宝当时人还在吉林老家,冯广庆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抓住这个热度,把舞厅打造成一个IP,“雅座可以卖咖啡和餐饮,把舞厅月票设计成可以收藏纪念的文创产品。”
冯广庆亲自为舞厅月票文创产品撰写了文案,他透露,目前文创产品项目已经在策划阶段,准备运作了,“以后这个舞厅就是‘漠河舞厅’的发祥地,漠河每一个舞厅都是漠河舞厅。”
李金宝不懂传播,也搞不清楚什么是文创和IP,他决定把舞厅继续开下去,最重要的是要为老人们保留一个舞池,让舞友们以后还可以在这里跳舞。也许,卡座和月票会成为外地游客追忆一个爱情故事的载体,也许,会有年轻人走进舞厅,像2019年12月的柳爽走进舞厅一样,加入正在跳舞的老人们,听他们讲那场大火的故事。
11月9日下午,李金宝在舞友群里发了一个通知:“今天晚上舞厅开门”。这是关了约半个月后,舞厅首次开张,沉寂多时的微信群活跃起来。
傍晚7点多,二十多个舞友拎着装舞鞋的包如约而至,赶赴这场久违的舞会。室外温度零下二十摄氏度,他们寒暄着坐在卡座上换掉厚厚的棉鞋,穿上皮鞋,几位女士还郑重其事地穿了长裙,每个人脸上戴着口罩,看不清表情。灯光音乐一起,他们旋入了舞池。
新京报记者 李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