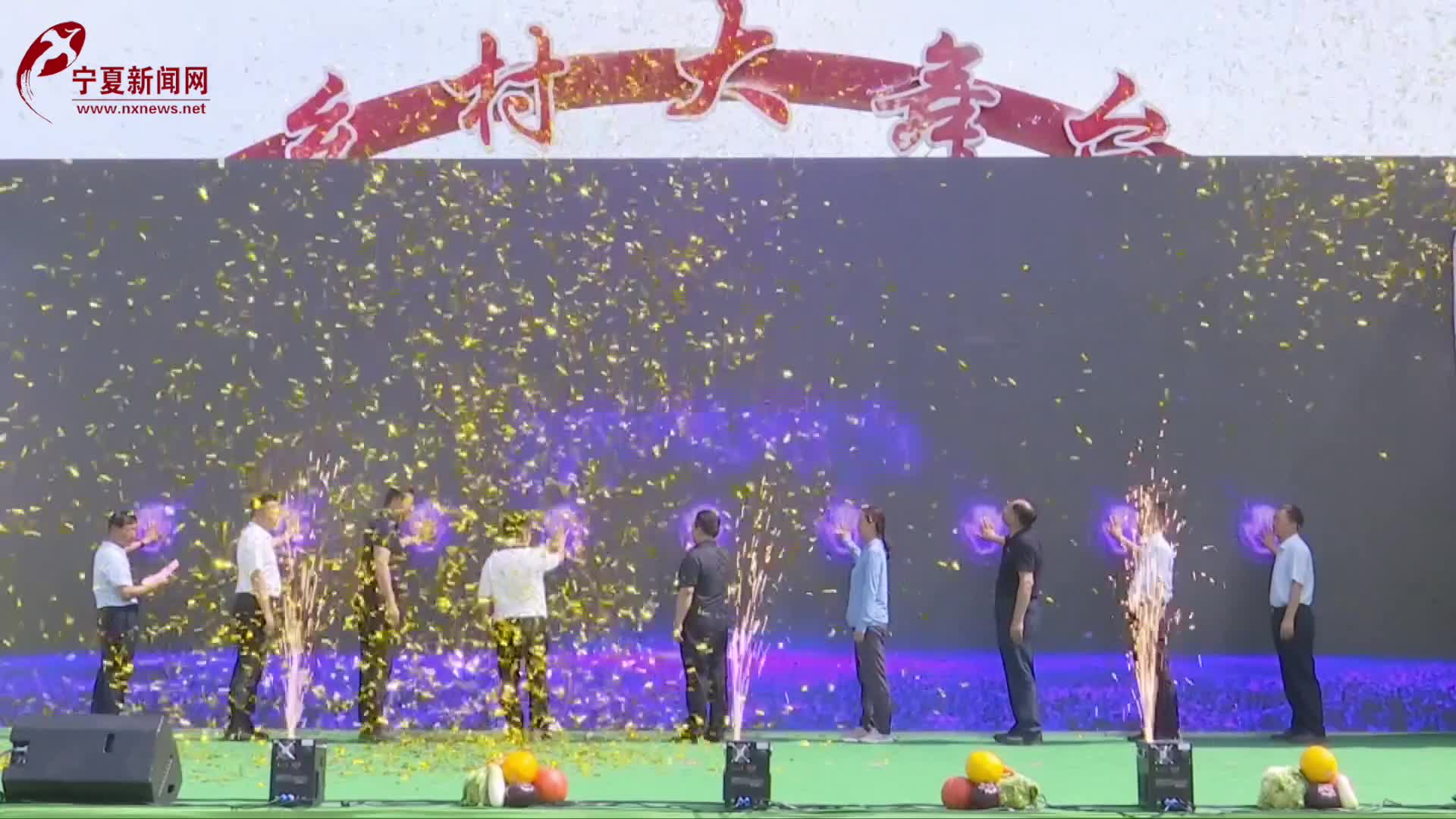西双版纳的象医生和“象爸爸”
来到这里的野象几乎都曾陷入某种危险。
在打斗中落败的公象,滚落八十多米高的山崖;刚出生身体孱弱的幼象,被母象用鼻子卷起送到了山下的村寨;还有摔落泥塘与蓄水池的,被对付野猪的陷阱与夹子困住的野象们。
它们被带到勐养片区的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现在这里,有7头被救助、收容的野象。
负责这一项目的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所所长、高级工程师沈庆仲。他介绍,2005年,救助中心成功救治了一头受伤的野象——被兽夹夹住左后腿的母象“然然”,至今该中心已参与24次救助亚洲象行动。
实际上,对于亚洲象的救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败的次数远多过成功。
“特别是对哺乳期小象的救助,目前都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沈庆仲说,每一次的救助,都是一次探索的过程,也为下一次的救助提供经验,“救助它们,让它们回归野外,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幼象“羊妞”
“羊妞”崴伤了脚。
5月底的一天,它进山玩耍,被凸起的树根绊倒。抹药、输液近一个月,左前腿依然红肿未消,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
“大象医生”保明伟仔细检查发现没扭伤骨头,他配了一盆消肿止痛的紫色药水,“羊妞”以为是个新玩具,脚在药水里晃来晃去,不时发出短促、欢快的叫声。
“羊妞”住在救助中心已六年。它胆子小,夜里其他野象的吼叫、公路上的车鸣,都可能惊吓到它,出现身体抽搐、上吐下泻的症状。“象爸爸”李涛说,它经常需要整晚的守护,摸着它,安抚它。
2015年8月,在普洱市思茅区橄榄坝村一户人家院落里被发现时,“羊妞”虚弱到几乎站不起来。保明伟记得,当时它的脐带伤口感染化脓,导致腹腔多处溃烂,身上还凸起多个鹅蛋大小的肿块。他推断,这是一头刚出生一周左右的幼象。
在救助中心,“羊妞”被安置在一间空旷的屋子里,角落里摆着一张高低床,四名饲养员轮班照顾它。
保明伟和从昆明赶来的兽医专家一起为它处理伤口,做了内科外科的检查,初步诊断,它还患有心律不齐、心力衰竭等症状。来自泰国的大象专家也赶了过来,商定救治方案。
幼象还没长臼齿,只能喝奶。有专家提到羊奶的营养接近象奶,保明伟就找来几只羊养在救助中心。“羊妞”的名字便这样喊了起来。
但它还没学会使用象鼻,喝水时鼻子软绵绵地垂着,挡住了嘴,“象爸爸”陈继铭记得,当时得用手托起象鼻,用奶瓶喂它喝,它一次只能喝十几毫升,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喂一次。
经过大半个月的救治,“羊妞”慢慢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打包票能真正救活它。毕竟国内外的兽医专家甚至给它下过“死亡通知书”。
沈庆仲说,“羊妞”来救助中心前,国内还没有哺乳期幼象被成功救护的案例,更何况,“羊妞”是被救助时年纪最小的幼象。
救助远比想象得难
参与野象救助工作三十余年,沈庆仲数不清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曾“捡”到过多少次幼象。遗憾的是,救助远比想象得难。有的在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有的抢救了40多天,依然没能抢救过来,有的幼象在救助站成长到三四岁,最终还是夭折了。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曹孟良介绍,1988年,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在勐养片区三岔河保护站成立了一间简易救助站,配备了两名工作人员,但没有专业的兽医。
1989年7月,勐养片区救助站接收了第一只受困的幼象。那是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幼象,掉进了一处山体塌方形成的泥土坑里。
没人知道该如何喂养一头幼象。工作人员比照着其他动物幼崽的喂养方式,端来大盆水和牛奶,试图喂给它。“就这样养了下来。”曹孟良给它取了个名字,“勐勐”。
原本计划着等“勐勐”长大一点便放归野外。曹孟良回忆,等到第三年左右,“勐勐”长到了500多公斤,突然生病了,瘫倒在地爬不起来,逐渐无法进食,全身溃烂。
救助站找来了兽医,还从昆明动物园请来兽医专家,都找不出病因。曹孟良分析,“被遗弃的小象可能带有一些先天性疾病,这可能是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自然淘汰的一个方式。”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野象走出保护区,到农地里取食农作物。不时有野象掉进农民挖的蓄水池,爬不出来。西双版纳州林草局野保站站长李中员记得,有村民找来村里最大的竹篾,兜住大象,绑上粗绳索,像拔河比赛一样,人抱住人,往后拖,就这样将这头庞然大物捞了出来。
1998年秋季,勐腊县南坪村的护林员赵金清在自家的稻田里发现了一头重伤的野象,它的腹部撕裂开一道口子,右后腿部也有明显的伤口。
赵金清看着野象一天天行动缓慢,虚弱下去。成群的蝇虫环绕着这头庞然大物,赵金清甚至能闻到腐肉散发出来腥臭味。
赵金清根据养牛的经验尝试救治这头野象。他买了消炎和驱虫的药。药驱赶走蝇虫,但野象的伤口肉眼可见地更加严重。后来保护区请来兽医专家。但依然没有效果,野象最终倒在了稻田里。
沈庆仲说,当时本地的兽医基本都是与家养的牲畜打交道,国内也没有专门研究和救治野象的兽医,只能请来国外的兽医专家指导。
沈庆仲意识到,对于野象的救助,缺失了重要的一环——专业的大象医生。
大象医生
2000年,沈庆仲招聘了云南省畜牧兽医学校的三名毕业生,安排在野象谷景区工作,保明伟便是其中之一。
2005年,保明伟首次参与救助一头受伤的小象。它被发现在野象谷附近硝塘,左后腿夹着一只兽夹,吃力地跟着象群走。
观察了几天,这头小象越走越慢,被母象推着跟在队尾。带着麻醉枪的兽医专家瞅准机会,把小象麻倒。象群受惊了,七八头母象围过来,用鼻子扒拉着它,试图托起它,不肯离开。
麻醉药效只能持续一个小时,救治时间紧迫,不得已用上了防暴弹和催泪弹,象群一跑开,几十号人冲过去,将小象挪上担架,抬到勐养片区的救助站。
小象有了名字,“然然”。拆开兽夹,左后腿上伤口深可见骨,皮肉已化脓感染。简单清洗、消炎后,麻醉药效就快到了,兽医们赶紧退出房间。小象一站起来便往人的方向冲,不断撞着笼子。它不吃不喝,丢进去的甘蔗它看都不看,还用鼻子将水桶打翻。
伤口发炎可能导致败血症,但兽医无法对它进行治疗,刚要靠近,它鼻子一甩打在兽医头上。
一些国外专家建议可以实施安乐死。保明伟不赞同,他觉得小象的攻击性强,正是因为它的求生意志。
“驯象师”熊朝永第一次见到“然然”时,它的耳朵和尾巴都竖起,目光凶狠,熊朝永知道这是一种警戒状态。它被关进有铁栏杆的象舍,栏杆能阻挡住野象,也能让“象爸爸”从中穿过。
熊朝永站在铁栏外,跨进去一步,将食物往小象身边送,送过去后马上退回来。就这样不远不近地投喂了快两周,它才允许了他的接近。
有了饲养员的配合,保明伟将外用的药装进一支高压喷雾器,趁着熊朝永吸引开“然然”的注意力,他拿着喷雾器对着“然然”的腿猛喷几下,然后赶紧跑开。他还改造了一支吹管,能站在相隔一二十米远处,将药“吹”射进去。
上药的问题得到解决,“然然”的伤口很快长出新肉。它对人的戒备放松了,“大象医生”保明伟也能接近它,记录下各项身体指征。
一开始,保明伟将数据与人的对比,简单判断“然然”是不是发烧,或有炎症。到后来采集的数据越来越多,他对比不同数据下“然然”的状态,总结出一套适用于野象的指标。
“可能不是百分百准确,但起码可以在救治过程中,提供一个参考标准。”保明伟笑了笑。
有了救治“然然”的经验,救助中心每年都有一两次救助成功的案例。2007年时,他们救助了一头重伤的母象“平平”。“平平”是在哺乳期时,被发情期的公象所伤。护林员赵金清发现它时,它臀部撕裂开一道长伤口,双腿浸满血色的脓水。
保明伟和国内外的兽医专家、妇科医生共同完成的这场手术,极其棘手。人类的医用仪器、B超设备等都拿到现场,根本无法穿透厚厚的象皮,当时甚至很难明确它身体内部的伤情。
保明伟记得,手术做了四次,一层一层刮去伤口的腐肉,摸索着手术,直到它的身体指征趋向于他总结的正常区间。
“平平”的手术应该算是成功了,但它失去了生育能力,伴随终身尿失禁。
沈庆仲将这个案例记录下来,分享给护林员与监测员,希望能应用到亚洲象的保护工作。“如果发现发情期的公象被母象拒绝,产生冲突时,我们可以马上有一些应对措施,一旦出现了伤害,我们能很快介入,进行治疗,可能情况不至于这么严重。”
随着救助野象的案例增多,保明伟的野象“病例库”在不断更新。
“象爸爸”
2008年,救助中心的象舍建成,“然然”和刚做完手术的“平平”住了进去。
后来,又有了和公象打斗掉落悬崖被抢救回来的“昆六”;一岁便离群的孤象“小强”;闯入普洱市区游荡几天的“阿宝”;砸坏十几辆车的“维吒哟”。
它们有了名字,有了自己的象舍,也有了专属的饲养员。
留下来的饲养员人不多。来救助中心应聘的人最开始都满怀热情和对大象的爱心,有些在动物园做过大象饲养员,有些是学养殖的学生,也有附近村寨的村民。陈继铭回忆,有的饲养员干了几个月,刚和大象熟悉起来便离开了,有的被野生动物园高薪挖走。
再有来应聘的新员工时,陈继铭会在最开始就泼下冷水,“大象看着很可爱,很温顺,但实际上,这份工作又苦又累又危险,你能坚持下去吗?”
在与野象朝夕相处中,饲养员有了个称号,“象爸爸”,这个名字为这份工作赋予了责任与感情。
大象开始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比如傣语的“Mai”(来)、“Bai”(去),可以配合保明伟的检查,张开口腔,抬起象蹄,甚至能区分自己的饲养员和其他象的饲养员。它们开始亲近人类,依赖人类。
救助中心坐落在勐养片区的中心位置,四面环山,临近三岔河一条支流,时常还有野象经过这里。
沈庆仲对比观察救助中心的象与附近的象群的活动,发现野象总在行走,一个象群每天可能移动10公里,食物条件不好的时候,可能走到15至20公里。他很快意识到,野象不能一直被关在狭窄的象舍,也不能只吃人类提供的几种食物,而要将它们放养到野外,吃多样的植物,“在自然中得到体质的锻炼”。
救助中心的象开始在保护区内小范围地活动。
但大象们似乎适应了圈养生活,不愿离开象舍。每天早晨,一名“象爸爸”需要拿着胡萝卜诱惑它往外走,另一名“象爸爸”牵引着它的耳朵,带着它往前走,傍晚再领回象舍,表现得好,就能得到食物的奖励。
一走出象舍,它们就撒了欢似的往山里走,但跑几步就要停下来等着“象爸爸”。进了山,找到一片草地,开始边走边吃。象走走停停,“象爸爸”也走走停停,每天得走上两三万步。
保明伟有些矛盾,在治疗过程中,野象开始信任人,依赖人,甚至离不开人,“但救助的野象,终归有一天要回到野外生存。”
放归难题
救助中心的象舍几乎住满了。除了被救助、收容的野象,这里还承担着亚洲象繁育的工作,至今已有9头小象在这里出生。
沈庆仲认为,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的增加,对于亚洲象的救助必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救助中心将作为“大象医院”的性质存在。
但事实上,直到现在,在野象的救助工作上,救助中心依然在面对失败,面对死亡。“亚洲象的救助,特别是对于哺乳期幼象的救助,是一个世界难题。”早在多年前,救助中心就开始尝试与高校、科研机构和医院合作,开展一些关于亚洲象的基础研究。但沈庆仲坦言,“我们对于亚洲象的认识和了解太少了,救助还在很初级的阶段。”
曹孟良提出过质疑,现在的救助模式,让野象已经完全依赖于人,每年举办的大象节上,摆着水果盛宴,非常隆重,这是不是改变了救助的目的?
“救助中心建立的初衷,应该是野象遇到困难或危险时,为它们提供救助,而它的困难解决了,救助完成了,最终还是让它健康地回归大自然中,救助是保护亚洲象的一项工作。”他说。
实际上,沈庆仲说,近年来,救助中心一直在不断探索、设计野象的放归路线。
但救助中心的野象几乎很难再适应野外。“羊妞”和“小强”几乎从小就在救助中心长大,它们与人相处的时间比象还多,在野外偶然碰上象群时,它们跑得比“象爸爸”还快。
而其他经历过重伤的野象,旧疾随时可能复发。比如“然然”,保明伟记不清它的伤疤撕裂过多少次,在野外活动时,遇上稍微陡峭的坡,动作一大,它的伤疤就可能撕裂。
沈庆仲认为,客观上,现在救助中心同样不具备放归野外的条件。在放归前,首先要对野象做长期的野化训练,还要能够监测它们回归自然后适应得怎么样,能不能生存。只有等到条件成熟后,救助中心可以向国家林业部门申请专家评估,判断是否能进行放归。
“放归一定是我们救助野象的最终目标。但这不是简单地把它拉到几百公里以外的森林就行的事情。贸然放回自然,很可能就是野象快要死亡的那一天了。”沈庆仲说,“在救助野象这件事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继铭想象过无数次放归“羊妞”的场景。他总担心“羊妞”会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境,但他心里清楚,那一天终会到来,“羊妞”终归要回到野外,“我期待着它带着它的宝宝回来看我的那一天,到时候我才能说,对它的救助,算是真正成功了。”
6月27日-30日
象群持续在峨山县塔甸镇附近林地内活动。省级指挥部要求继续做好盯象、管人、理赔、助迁工作。独象位于象群东北方向,距离象群53.6公里,在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附近林地内活动。
7月1日-4日
象群进入化念镇并持续活动。
7月5日-6日
象群继续南迁,进入新平县桂山街道附近林地内活动、休息。独象位于象群东北方向,距离象群70公里左右,在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附近活动。15头象均在监测范围内,人象平安。
7月7日15时
独象安全回归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片区栖息地。
7月5日以来,该象进入玉溪市北城街道拶[zǎn]坝塘社区,距晋红高速仅0.3公里,距昆玉城际铁路仅0.2公里,独象安全管控难度大,公共安全风险高。为确保人象安全,经研判,现场指挥部按照应急处置预案,对其采取了捕捉措施。7月7日15时,独象已安全转移至其原栖息地,各项生理指标正常,安全回归栖息地。
北移离群独象于今年6月6日脱离北移亚洲象群,已独自活动32天。
7月11日
象群已南迁至红河州石屏县龙武镇,在附近林地内活动。象群在监测范围内,人象平安。
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