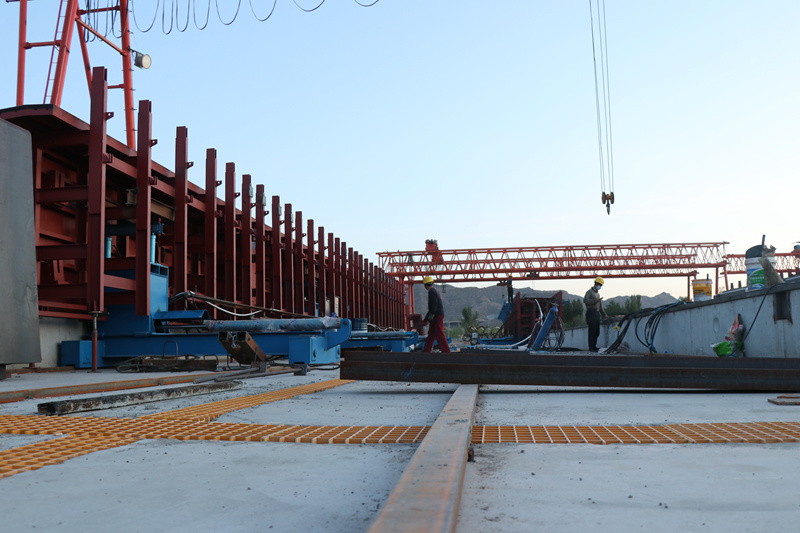天津理工大学的校园面积不小,教学楼都是整齐统一的砖红色,初来乍到的人容易迷路。但如果你问聋人工学院怎么走,连东门口咖啡厅入职不久的店员,都能为你准确定位。在这里,没人不知道这座被誉为“聋人小清华”的学院。
聋人工学院是中国第一所、世界第四所面向聋人的高等工科特殊教育学院。从1991年,其前身天津大学机电分校特殊教育部(简称特教部)成立并招收首届学生算起,聋人工学院开启并见证了中国聋人高等工科教育30年的发展历程。如今,学院教学楼立于校园西侧,这栋2013年投入使用的建筑,像楼前刚长到碗口粗的树木一样正当年少,一层墙上“中国梦也是残疾人的梦”十个大字红得鲜亮。三十载光阴流转的印记则被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
教学楼的五层,有一面长长的照片墙,各届学生的毕业合影都被张贴于此。像素越来越高、年份越来越近,青春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穿着从白色的确良衬衫渐变成黑底学士服;院里的老师们接力般笑眯眯守在前排,有的从青丝满头守到华发渐生。
更详尽的学生档案,存在老师的脑海里。他们不仅记得这些孩子从哪里考来、毕业后去了哪里,还记得他们失去听力的年纪和原因,甚至记得谁为了省钱总不好好吃饭……
“手语版国歌”研制者:基础都是在这儿打的
1992年9月,从山西太谷考来天津读书的“学霸”少年陈华铭,平生第三次“懵了”。
那一年,特教部首次走出天津,在全国5个试点省市招收聋人学生,陈华铭赶上了。但直到他放下行囊走进教室,才意识到自己是同级11名听障生中,唯一完全不会手语的人。
身边的同学大多来自聋校,手语就是他们的母语,用起来得心应手,很快“打”成一片。而一路都在普通学校和健听人(听力健全人,也称“听人”)一起学习的陈华铭,“什么也不懂,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他看懵了。
这种感觉,就像9岁的某天,陈华铭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睡懵了”:家里人冲他讲话,全都干张嘴不出声。他以为爸妈在跟他开玩笑,却没想到,开玩笑的是“无故没收”他听力的老天爷。
二十多年后,陈华铭已经出任天津市聋人协会会长。他邀请耳鼻喉科专家为当地聋人做基因检测,分析致聋因素。交流过程中,他向医生聊起儿时经历,对方做出判断:9岁那年一场腮腺炎引起的高烧,应该就是导致他听力损失的原因——但在当年,受医疗条件的限制,没有一个医生能给出这样明确的结论。
在学校,陈华铭一直是好学生,不难想象,一个习惯了名列前茅的孩子,发现自己“上课听不见老师讲啥,下课没法和同学交流”时,是怎样的无助和孤独。但学习,或许是引他冲破无声世界的唯一出路。
陈华铭的听力损失严重,但发音说话的能力还在。他用眼睛和手代替耳朵,靠课前看教材,课上盯板书,课下抄同学笔记来学习。遇到不懂的内容,就追着老师问。听不到老师的回答,他就跟老师“笔谈”,请老师把要说的话写下来,“总之弄不明白决不罢休。”
凭着这股劲儿,陈华铭的成绩“比失聪之前还提升了些”。几年后,他考上了家乡的重点高中。接下来,他还想考大学、做天之骄子。没几个人相信他能考上。他的高中老师都知道这个宿舍熄灯后还点着蜡烛做题的聋人学生有多不容易,因而各尽所能地帮他。但提到高考,老师也摇头,“正常人能有几个考上大学的?你一个聋孩子,说不准。”
眼看距离高考还剩4个月,爱开玩笑的老天爷在陈华铭打篮球时绊倒了他。他“摔懵了”,这次是真懵了,他被摔成重度脑震荡,昏迷了3个小时,在医院躺了两个星期。
伤没好利索,陈华铭依然执拗地参加了高考,却几无悬念地败下阵来。幸好打击和转机同时出现了——
1992年,创立满一年的特教部决定在天津、山西、山东、江苏、吉林招收聋人学生,于4月进行单独招生考试。他稀里糊涂报了名,只想着多个选择多条路。突击学了两个月的机械基础知识,陈华铭去天津参加了考试。
陈华铭有些意外地收到了来自特教部的录取通知书。因为相信自己“没什么做不到”,初到特教部时一度被手语“懵住”的陈华铭拜同学为师,边用边记,不仅把手语学成了,还出人意料地厉害。今年3月,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开幕会上,邰丽华委员用铿锵的手语“唱”起国歌,视频一时间刷屏朋友圈。更多的人由此得知了此前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家通用手语方案》。陈华铭就是方案研究小组的6名成员之一。他和其他组员一起,把国歌歌词拆解成不同的词条,又天南地北地收集了60多种“手语方言”版国歌。在不同字词的手语打法间逐个比选,最终形成了那个让全国人民为之泪目的标准版。
“这都是在聋人工学院打的底子好。”陈华铭笑着说。
比辞海还厚的档案,像妈妈一样的老师
“一年级获二等奖学金、1993年获天津市理工科优秀奖学金、三年级获一等奖学金、1994年(获评)校级优秀学生干部、1995年转入本科(学习)、(同年通过)计算机一级考试……”
陈华铭当年的荣誉,汪美林全都白纸黑字地替他记在了“档案”里。
1991年,一直在天津大学机电分校院长办公室工作的汪美林被抽调到刚刚组建的特教部担任行政副主任。她在这个岗位上干了7年,从零开始研究特殊教育,掏心掏肺手把手地带了6届83名聋人大学生,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聋人高等工科教育从无到有的过程。
从1991年9月11日特教部成立,首批6名聋生入学;到1996年4月26日,《国务院批转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的通知》发布,“创办天津聋人工学院”被明确列入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再到1997年11月5日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正式挂牌,每一个重大的时间节点,她都在现场。
不仅在场,她还把关键时刻和孩子们的成长足迹一并记录下来——特教部的新闻剪报、重要文件的复印件,学生的证件照和生活照、奖状复印件还有写给她的信,她都留着,还在空白处认认真真做好批注——7年,2555天,这本凝结着汪美林心血的“自制”档案,厚度超过了辞海。
汪美林今年67岁,早就退休了。得知记者来采访,她从箱子底把这本资料抱了出来,“这都是历史!”
在这本“历史”的前几页写着一句话,“不管困难多大,阻力多大,也要把高等工科特殊教育办起来,培养出我国自己的聋人工科大学生。”说这话的人是时任天津大学机电分校校长、激光专家巴恩旭教授。
1991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正式施行,残疾人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受此启发,巴恩旭教授提出了创办高等工科特殊教育的大胆设想,让中国聋人也能发挥形象思维好、动手能力强的优势,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陈华铭是汪美林迎进校园的第二届学生。时隔20多年,这对师生分别向记者提到对方,声音都激动地抬高了八度。“这是华铭!这也是华铭!你快都拍下来发给他看看。”汪美林嗓门儿大、天津口音纯正,她翻着厚厚的档案簿,找到陈华铭的照片就兴奋地指给记者看。
当年,陈华铭和两名同学从特教部大专毕业后,想转入机械专业的本科班继续就读。他们的想法受到了不少质疑:“特教部的学生,学得再好,能和普通学生一起上课吗?”但汪美林不管这一套,她让学生们写好申请,自己去帮他们跑手续。她没跟学生说过个中的辛苦,但陈华铭知道,“汪老师为我们跑了不少趟、求了不少人”。三个学生成功转入本科学习。怕孩子们跟不上,每当他们有课,特教部都会抽调一位老师陪他们一起听,有不理解的地方,回来再配合手语一点点教。
“汪老师是我的恩师,人一生能碰到一个特别负责、把学生当孩子的老师,那是非常大的荣幸。”陈华铭言及汪美林,满是敬重。
记着学生的一切,忘了自己是“领导”
30年一晃而过,当初的特教部已经发展为拥有4个专业、6个全纳教育专业、3个研究生专业的“聋人小清华”。新一代的“聋工人”对汪美林大多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汪美林和聋人工科教育开拓者当年坚持的很多东西,却如无形资产般传了下来。
王晓鸥是“80后”,今年是他在聋人工学院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按照学院每年100人左右的招生规模来算,从2011年担任学院专职辅导员到现在,他见证了超过1000名听障生的成长历程。虽然没有用纸笔记录,但他的脑海里,也存着一本厚厚的学生档案。
记者请这位资深辅导员推荐几位学生代表作为采访对象,他开始“调档”——闭上眼睛,短暂思考,然后报出一个名字:“在校生的话,梁一帆吧。普校毕业,2016年从河南考过来,学的是艺术专业产品设计方向。发音是从小练的,讲话很清楚,手语是本科阶段现学的。现在手语、口语交流都没问题,还能做手语翻译。全国第十届残运会闭幕式的时候,她做过舞蹈手语指挥;疫情期间还给武汉的聋人录过防疫的手语视频。她评上了2019年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2020年我们学院有了首批单考单招的硕士研究生,她刚毕业又考回来了。”
“全纳专业的毕业生……我们的全纳专业是2013年开始招生的,因为要和健听生一起在其他学院上专业课,所以招的都是听力、口语好一些的学生。第一届有个学财务管理的学生刚毕业就被渣打银行定向招走了,但我得看看,我把她的QQ号存哪儿了。您要是着急采访的话,可以先联系吴俊玮,现在上大四,专业是工程造价。适应能力很强、成绩也不错,还帮着老师做一些学院的党务工作。”
记者惊异于王晓鸥对学生的了解程度。近几年加入聋人工学院的年轻辅导员们,私底下都管他叫“大神”。因为他手语好,更因为他对学生的用心和关注。王晓鸥每周要上两堂思政课,学生党务等日常工作也由他负责。即便日程表已经排得很满,碰到学生身体不舒服,他还要挤出时间陪孩子们去看医生,“一般的头疼脑热其他辅导员带着去就行,要是比较严重或者病因复杂一些的还得我去,要不万一症状翻译得不准,就出大事了。”
因为听障生群体的身体情况、思想情况、口语和手语水平各有不同,所以聋人工学院在制定教学和帮扶计划时,特别强调“一生一策”。“每个学生的情况,我们都要记清楚。”
王晓鸥唯一记不清的,大概就是自己的职务了。“现在……应该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他说在聋人工学院,主要负责讲课的叫老师,做学生工作的叫辅导员,所有人都时刻准备着为听障生服务,“没有什么领导的概念”。
按照王晓鸥提供的学生代表名单,记者开始联系采访对象。
梁一帆和张淇轩都是聋人工学院未来制造设计工坊的成员,接通视频电话的时候,他们正在成都参加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我们的作品叫《艺术与科技共舞》,刚拿了艺术实践工作坊类一等奖。”梁一帆白净的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可能因为激动,她的语速挺快,除了吐字时偶尔加重的鼻音,你很难意识到她是一个听障生。她自己倒不避讳,用流畅的手语把记者的问题翻译给张淇轩看。“没什么好避讳的啊,我们就是很普通的聋人学生。”
吴俊玮今年大四,谈起毕业找工作的事,他显得胸有成竹。“工程造价是一个新兴学科专业,在国内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且工程造价专业的开拓者就来自我们天津理工,我对自己的就业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这是有意义的工作,我乐意来”
最后一位学生代表没有出现在最初的采访名单上,她叫王慧,聋人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2015届毕业生。王慧是天津宝坻人,大学毕业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宝坻,无论求职之旅还是人生之路,似乎都退回了原点,她和母校的老师同学也就此少了联系。
大半年前,在宝坻区残联的介绍下,王慧在当地一家助残就业基地找到了工作。这个名为“阳光福乐多”的助残基地同时还是一家养老院,140多个老人和近50个有智力障碍的青少年生活在同一个大院里。创办人田丽超依托着自家开的养老院,几乎靠贴钱为这40多个家境清寒的残障孩子撑起了一方天地,对他们进行简单的职业培训,让他们学着用双手养活自己。
王慧去应聘的时候,田丽超正在忙活一件大事,她要帮基地里智力残疾程度较轻的孩子掌握洗衣熨烫设备的操作方法,再为他们开一家对外营业的洗衣店,“将来让孩子们赚上工资、交上社保!”这个美好的设想当时还停留在初始阶段——洗衣设备已经拉进了院、通上了电,孩子们也兴奋地系上了统一的白围裙,但在熟悉这些“大家伙”动辄20步以上的作业流程之前,他们只能拿自己和熟人的衣服“练手”。
田丽超想把指导孩子使用设备的任务交给王慧,但她也很清楚,“有花销没进账”的局面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她没办法给王慧开出与“天津理工大学毕业生”身份相匹配的工资。田丽超开门见山地给王慧发微信,“我们这儿能留住你吗?”王慧回得也直接,“能留住。这是有意义的工作,我乐意来!”
今年1月,记者到“阳光福乐多”采访田丽超时,偶然遇到了王慧。她守在熨烫机前,看基地里的小伙子熨一件西服。王慧比小伙子矮一头还多,神态却像个教孩子做家务的妈妈:只看不出声,但毛衣袖子已经撸上去了,仿佛时刻准备着,一旦出现问题,迅速上手帮忙。
“她真就像个母亲一样!”田丽超说,基地里的孩子们智力有障碍,却能准确地判断谁是真心待他们好,所以才“没有一个孩子不喜欢王慧的”。田丽超于是放心地把更多工作交给王慧,让她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
最近,王慧新接手了一项任务。他们的洗衣房快要正式营业了,王慧负责教基地里的孩子们跳舞,到开张那天表演给大家看。
“阳光福乐多”有自己的短视频账号,田丽超会把孩子们生活中的小趣事、小才艺传上去。这次的舞蹈,无疑将成为一段“重磅视频”。王慧一点也不敢马虎,像当年聋人工学院舞蹈队的老师那样,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纠正动作。
田丽超说,尽管手头的活儿越来越多,但王慧从没跟她说过,“我是残疾人,你们应该特殊照顾我!”相反,王慧给她发微信表过态,“会干的活儿我都愿意干;不会干的,我愿意学。”教孩子舞蹈,显然是王慧“会干的”,田丽超兴奋地给记者形容,“她跳起来可漂亮啦!”
后来,记者把这个不太符合世俗成功学标准的故事,讲给了聋人工学院几位记得王慧的老师。听完,所有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健谈的英语老师李子刚抬起头来,笑着说,干了近二十年的聋人教师,他常告诉学生,盼着他们能够“从聋到龙”,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融入社会、自食其力;也常鼓励他们再走远些,去更大的舞台上试试身手。但他心里,还一直藏着个有些奢侈的愿望,“都说老师是蜡烛,可以照亮孩子的人生。我就盼着我们学院教出来的学生,都能变成小小的光源,照亮他们身边的人,哪怕只有几个也好。让光亮传递下去,才是当老师最大的意义。”
李子刚总鼓励学生们要“从聋到龙”,却不好意思把“成为光”挂在嘴边,因为他知道那太难了,“健听人也很难做到。”但他和同事们却惊喜地发现,这三十年间,有许多从聋人工学院出发的学子,用各自的方式实现或者接近这个目标。
“王慧做到了。”李子刚看着记者,语气郑重、眼光温柔,像汪美林说起陈华铭,“她是我的骄傲。”(记者雷琨、白佳丽、张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