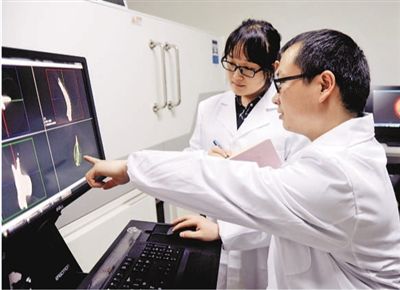最近由作家陈彦小说《装台》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让不少观众与读者将目光再次聚焦于陕西文学与文化。其实,在2019年陈彦获得茅盾文学奖之时,就有观察者认为,陕西文学的精神脉络没有中断,陕西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上依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电视剧的播出再次将其推向热潮。
陕西文学的精神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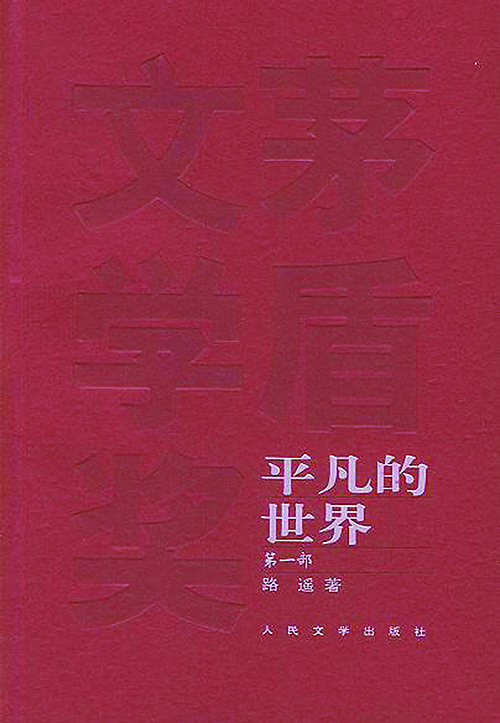
不可否认,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文学趣味、思维方式乃至精神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在鲁迅的小说里看到浙江的风俗文化,在沈从文的笔下触摸湘西的独特风情,至于像莫言构建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也早就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但是,能像陕西文学这样以一个省域范围来构建的“文学版图”,其实并不多见。
因为,即便是在一个省内的作家及其作品,往往也有较强的差异性。比如,我们很少听到“山东文学”这个概念,即便在所谓的“北京文学”“广东文学”内部,也是风格迥异,绝非“铁板一块”——但是,陕西文学却经常被当成一个整体的概念而提出。这到底是为什么?
首先,陕西文学具有很强的、很明显的精神传承脉络,甚至连作家的年龄序列都能前后相继,有一个很清晰的传承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陕西文学有柳青、杜鹏程等知名作家,写下了《创业史》《保卫延安》等经典的红色文学。在“十七年文学”(1949年—1966年)的历史脉络中,这一批陕西文学作家是以强烈的革命叙事与想象而留名的,尤其是《创业史》这样的经典作品,不仅是文学史上的大作,也是后世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征候的重要文本。关于这些作品的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也早已蔚为大观,其中最关键的理解路径,就是这些红色文学不仅图解了一些政治政策,它们与当时国人的“情感结构”也密切相关。因此,即便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文学技法可能不够“先锋”,但它们以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与对时代精神的理解而获得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陕西文学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显然是路遥。《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两部作品都早就成为时代的经典之作,路遥的作品延续了之前陕西文学强烈的现实主义传统风格。这个风格在文本里,一个是表现为题材十分“接地气”,关注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下的跌宕命运,另一个关键表现则是写法上比较保守,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末先锋文学已经成为文坛“时髦”的时候,路遥依然用最中规中矩、朴实无华的叙事方法来创作《平凡的世界》。即便文坛喧哗热闹,但陕西文学似乎一直坚守着从延安文艺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路径,如同这些作家脚下的那篇黄土地,看起来并无惊人的风采,却有着最扎实最勤勉的文学实践。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老一批陕西作家的去世或淡出,以贾平凹、陈忠实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全面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一度引起关注的“陕军东征”现象。1993年,《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发表文章《“陕军东征”火爆京城》,让整个文坛都注意到了陕西文学的最新动向——《废都》《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和《热爱命运》五部小说在这一年被推出,这种“集体亮相”的方式,在文坛上已经许久没出现了。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当属贾平凹《废都》与陈忠实《白鹿原》。前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也让贾平凹一度走到了舆论的风头浪尖上。直至今天,《废都》依然是我们了解上世纪90年代文学史与文化现象时,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文本。
这并非因为《废都》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超越他者,其实《废都》中不乏各种粗糙之处,一些内容对女性读者似乎也不太友好。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废都》的背后正是那个浮躁的年代,当中国社会猛然进入商品经济大潮后,传统的文化理想与人文关怀渐渐失落。《废都》正是那个历史特殊阶段的精神征候,虽然文本中不乏各种夸张乃至荒谬之处,但其文学冲击力与文学史上的“铭刻”痕迹,却是其他作品难以具备的特点。

从这一点上看,从《废都》开始,陕西作家的视角不再局限在乡土的世界,城市的光怪陆离与灯红酒绿,也成为作家们书写的重要对象。只是这些叙事的视角,往往依然延续着过去的“进城”叙事——这就不同于真正的城市文学,而是从城市化的角度来“审视”城市问题,这更像是转型时代特有的“进城”叙事路径。与此同时,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处理历史叙事的方法也与之前的红色经典很不一样,更具“再解读”风貌与人性关怀的历史观。当然,与之前的革命叙事一脉相承的是,它依然始终关怀着充满苦难与泥泞的土地,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在陕西文学中依然存在。
地域文学的突围之路
在中国诸多省级行政区中,陕西省具备本省特色的文学风貌,这点在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版图上十分明显。地域文化没有高下之分,但其各自的影响力却有不小的差别。而且,外界看待一个省域文学与文化的时候,还存在“打包”式的思维,比如东北三省的文学,往往就被混为一谈。尤其是近年随着一些新生代作品的诞生,文坛内外对“东北文学”有了更多认识与期待。
其实,“东北文学”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中国文学最有影响力的地域文学概念之一。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作家早就是文学史上的知名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的工业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计划经济与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也让东北文化众星荟萃。因此,即便在今天,一提到东北文学,人们都没法绕开工业、工人等问题,不论是它们曾经给予了东北文化极度的辉煌,还是后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东北人遇到的困境。与之相关的故事与情绪,不断形成东北人的“情感结构”——这是今天的东北文学依赖的精神土壤。而在东北三省之外,外界对东北文学却存在某些吊诡的想象。一方面,读者把东北想象成一个凋败的、灰色的世界,另一方面,又因为东北文学呈现的“铁锈”或者“怀旧”式的风格,而与其他正在现代化大道上狂飙突进的省域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这让不少读者对东北文学获得了某种“陌生化”的阅读快感与奇诡想象。
近年走红的青年作家班宇在其小说《冬泳》中呈现的冷寂与颓败,能成为不少人热衷的“东北文学形象”,不是没有现实缘由的。尽管这未必是东北完全真实的情况,但的确符合多数读者对东北的想象。其实,陕西文学从中或许也能获得某种启示。陕西文化在历史上也一度十分辉煌,千年帝都在这里,革命文化的传统也在这里,但在市场经济的活跃度与发展成果上,陕西却无法与东部沿海地区比肩。这种夹杂着历史荣光与现实困境的精神征候,其实与东北也有相似之处。
因此,当我们反思陕西文学的时候,需要在一个文学史的时间纵轴上看,也要在当前的地域文化版图的横轴上看,尤其是不妨参照东北文学的经验与现实,来寻找陕西文学的发展路径。在这其中,青年作家(尤其是70后到90后)的精神状态与文学趣味至关重要。文学的发展未必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某种程度上的历史与现实散发出的苦涩与伤痛,对文学创作者来说,或许还是一个精神的富矿。面对它们的时候,陕西文学前辈们的刚勇与执着,或许会给今天的观察者一些启发。
对陕西文学的反思
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植根于陕西浓厚的历史文化土壤。这其中既有延安文艺以来的精神传统,也有陕西文学强烈的乡土情结。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陕西的农村题材文学在全国文学版图里十分突出,大多数知名作家都来自农村,有着丰富的乡土生活经验。而且,他们的创作大多追求朴实的风格,很少借助现代主义来“艺术化”乡土生活。在这种风格影响下,陕西文学看起来似乎是朴素而不华丽的,却是真正“接地气”的,很多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生活,又供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普通读者来阅读品味。
陕西作家大多都是勤勉型的,他们大多不追求所谓的“天才与灵光”,而是让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在现实中寻找创作素材,又让创作来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甚至,像路遥这样的作家,可以算得上是“苦吟型”作家了。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曾说:“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过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获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这样的自我定位与文学志趣,我们在那些所谓的“轻写作”里很少见到,说“路遥是用生命在写作”也绝不夸张。事实上,路遥长年的伏案写作过早地透支了他的身体,他不幸成为盛年早逝的当代作家,恐怕与他心力交瘁的精神状态也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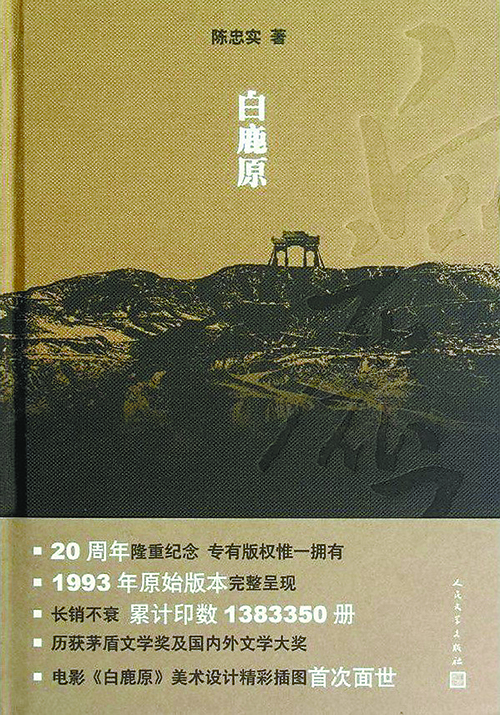
然而,这种极具现实感与使命感的精神状态,的确是以路遥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的风格。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也有构建“民族秘史”的巴尔扎克式的文学理想,这种追求宏大叙事与历史感、现实感的写作冲动,的确在今天看来十分难得。当我们流行的文学越来越追求一些所谓的“高妙技法”或者“文学机灵”的时候,不妨看看陕西文学前辈们那些看似“土里土气”实则淳朴踏实的做法。
那些直击灵魂深处的创作,即便不是“字字看来皆是血”,起码也要耗费作家大量的气血与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陕西文学一直没有放弃文学的社会价值,文以载道乃至“铁肩担道义”的文学观念,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急缺的精神。
当然,从更开阔的文学世界来看,陕西文学也存在自己的问题,它的特点与亮点当中也夹杂了一些缺陷与遗憾。比如,对心灵世界的深入探寻,以及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多样叙事,都是它存在的一些短板,或许在不远的将来,陕西文学在与其他地域文学交融之后,会呈现出更加多姿多彩的变化。(作者 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