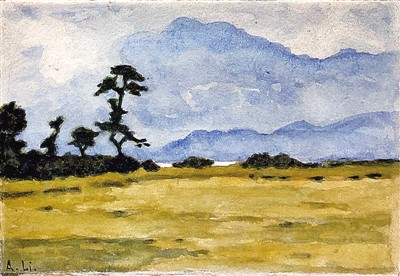不抵不抗,与之共舞,是法国人眼中的中国时间观
在中国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提醒柯思婷·佳玥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真知:生命的核心问题,是时间。而自从学了普通话,她又发现了中国人自己因为过分熟悉而不再有感的语言中的时间观:慢吃、慢走、不着急……
柯思婷·佳玥是一个法国人,在北京生活了17年,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她当过哲学老师、企业家、作家,自认最重要的身份是“中法文化的摆渡者”(现任中法文化论坛副主席)。她把这些年的所思所想,写成了《时间里的中国人》。
在西方的观念中,时间是线性的、可测的理性时间。这种时间观是工业革命以来,细分规划、加速挤压的结果。工业化追求速度,人们无法幸免地继承并感染了这种急性子,生活中也养成了“能不等就不等”的习惯。
佳玥觉得,中国人对待时间就多了一个感性的维度,能与时间成为朋友。“对于中国人而言,时间既不是一支射向靶子的飞箭,也不是一个度量流沙的沙漏,而是流水。水有时会吞噬我们,却又承载着我们、怀抱着我们;它似弱实强,任何物事都无法阻止它奔流入海。”
一个有趣的比喻:中国人的时间不像是“内衣”,属于个人财产;而像是“礼品”,在人需要时赠与。这种在分配时间上的慷慨,只能存在于这样一类文化,即时间被看作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这种区别,在很多细节中都能体现,比如,在法国,用餐前的礼貌用语是“祝您胃口好”,中国人说的是“请您慢用”。两者表达的都是对对方的关心,对进餐方式却有不同的期许,胃口好是要大快朵颐的,慢用是要细嚼慢咽的。
再比如,在西方的文化中,睡眠不是一件好事,它与懒惰、浪费相连,甚至与邪恶有关。书中附录有戈雅的版画:梦是可怕,心魔生焉。同样是睡眠,庄周梦蝶多么美好。
在中国古装剧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计时方式:一盏茶的时间、一炷香的时间。这种计时单位是有场景和氛围的,时间和优雅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抽象化之后,即便事件不存在,时间也照样有那个调性。
当然,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中国,也是一个人人皆匆匆的速度中国。但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文明中,有些东西不是按两下鼠标就能删净的。人们在行色匆匆的CBD十字街口,依然存在着与时间为友的天然意识。
有一次,佳玥在北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一个让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会议。桌子旁坐了12个人,只有她一个西方人。他们正在筹备一场文化论坛,要商量出一个日程,面前是一本夹着实施方案的红皮文件夹。佳玥在上面看到了一些具体的人名和时间安排,精确到分钟,一丝不苟的样子。突然,佳玥想起了什么,问道,那些纸上写好几点几分发言的人物都确认出场吗?对方平静地回答,没有,这是预案,一切要等到……
“像中国人那样对待时间,我学得很苦。他们或者不提前一周预约,或者比约会时间早 20 分钟就已经到了;或者来约会却没有具体的方案,或者约会时才告诉你一切都变了。我常被弄得昏头涨脑。”佳玥说。
时间观的不同,决定了一件事到底应该如何开展。就像一个中国书法家,万事俱备待挥毫,不是为了弄出一个个汉字,而是精气神的聚涌,重要的不是纸上汉字的意思,而是激情一时得自由。“在中国,时间像书法,书法在艺术中等级最高。”佳玥总结。
后来,佳玥放下“法国方式”,毅然决然地按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时间时,“反而发现了一种含而不露的智慧。在琐碎的日常行为中,在各种庆典礼节中,在中国人的聚会和笑声里,这种智慧悄然绽放”。
我总觉得,佳玥作为一个法国人看中国,有时候就像在中国一线城市的人看小城镇。尤其是当在一线城市工作的人,过年回了家,两地瞬间切换,这种感觉会更强烈。但这种“眼光”不存在俯视或者观察的意味,有可能是对渐渐消逝的田园生活的回望,也可能是在寻找一种古老的智慧。
在一个被时间裹挟的时代,人们开始重新发现自己。几年前,木心的那首《从前慢》突然流传在街坊闾巷,“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代人的一生能爱几个人不确定,但车、马、邮件肯定都是指数级地变快。
一辈子计算时间是很要命的事,文化堕落为计时器和进度表,其实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度过我们的时间。我还真是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得出了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晚年坐在躺椅上,腿已经动不了了,大把的时间就像在嘲笑自己,这时候再回忆过往,还有一些人和事,能让衰老的脸上浮起一丝动容。
就像书法的起势,笔没有落下的时候,书法家的眼前已是笔墨万千;当作品完成后,时间就成了唯一的评判者;既然终点是确定的,那节奏我们自己来。
在中国的生活中,佳玥特别喜欢广场舞: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既节奏整齐,又人人可参与。就如中国人对待时间,“不抵不抗,与之共舞”。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